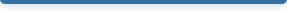彭馨葭 完权(语言研究所)
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1916年的《普通语言学教程》通常被视为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奠基之作。当前语言学界主要的研究取向,比如形式语言学、认知功能语言学、变异社会语言学的理论体系,基本是对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框架的延续、发展和迭代更新。这些发轫于西方国家、主要基于印欧语事实的理论目前依然是我国语言学研究的主要组成内容。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语言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来看,中国语言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建设还处于筚路蓝缕的阶段。中国语言学应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引领学科建设,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语言学”。
回望“马克思主义”和
“语言学”的相向而行
不少西方学者曾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结合起来。跨学科看,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等都从马克思主义视角关注过语言现象,这些理论本质是社会政治学研究,但也不乏对语言的洞见。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理论,以费尔克劳、范迪克等为代表的批判性话语分析对现实话语的研究更为深入,对语言本体研究的启发也更大。而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则是直接标举马克思主义取向的语言本体研究。
苏联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掀起“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的研究热潮,其标志性事件是斯大林1950年发表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受其影响,我国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也曾短暂地开展过“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研究的基础工作。一些高校和科研机构,比如北京大学中文系、吉林师范大学中文系整理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语言的论述并形成原著辑录,尝试探讨马克思主义立场的语言观。尽管其理论框架略显粗糙,引用说理的内容多于阐释说明的部分,但这些研究贵在将语言文字实践工作纳入语言学的学科体系中,是中国学界对马克思主义语言学学理化的初步探索。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语言学应赓续前辈学者的研究传统,建设具有中国立场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学学科。
学科建设的两大理论立场
“马克思主义语言学”,根据《王力语言学词典》的定义,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有关语言的学说,以及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为指导的语言学。这个定义,概括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语言学学科建设的两大理论立场。
一是形成系统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理论。首先,需要提炼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中与语言有关的核心议题,对相关观点进行梳理。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工程的成果之一,由卫志强编著的论述辑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语言》凝练形成了几大主题,包括语言的本质、语言的结构、语言的演变、语言与社会、语言与方言、语言与文化、语言与民族和宗教、语言的文风等,这些主题在建立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理论框架时可作为参考。其次,需要结合当前的社会现实和语言学实证研究的最新证据,对相关观点进行批判性的考察、检验、评价。例如,在语言的本质属性问题上,斯大林认为语言既不是上层建筑,也不是生产工具,那么,大语言模型所带来的变革是否挑战了以往对语言的理解?又如,关于语言的起源,恩格斯提出“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人类演化的最新研究对此是否支持?再者,对于现代语言学理论的核心理念,马克思主义立场会如何评价?比如,索绪尔对“语言”和“言语”的区分,语言的本质是不是一个抽象的符号系统,如何看待语言的发展演变,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理论需要回答的问题。
二是确立马克思主义语言学方法论。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研究属于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研究的一部分,共享其根本的立场、思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体系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根本方法,包括以实践为基础的研究方法、社会系统研究方法、社会矛盾研究方法等。这些研究方法对语言学主要的研究方法,比如内省法、田野调查法、实验法、问卷访谈法、语料库统计等方法如何进行指导、改造、更新,最终需要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语言学方法论上体现出来。
新时代如何建设
“中国马克思主义语言学”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的理论体系和实践行动指明了新的方向。中国马克思主义语言学学科建设可以从下面四个“坚持”入手。
首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打破印欧语眼光的束缚,坚持从汉语事实出发,立足中国实际做研究,而不是一味地追求语言学理论的普适性、对西方语言学理论生搬硬套。近年来,汉语学界如徐通锵的字本位理论、冯胜利的韵律句法、沈家煊的对言语法,都是中国语言学界坚持“第一个结合”的有益尝试。
其次,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要充分挖掘中国深厚的思想资源和丰富的语言文字资源,将其纳入中国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的理论体系中。索绪尔以来,言文分离是一个长期的传统。中国马克思主义语言学需要探讨如何提升书面文字和口头语言结合研究的高度,特别是重视我国以汉字学、中国民族古文字为代表的中国文字学的优秀资源和成果经验。汉字对汉语构词造句的影响,有力驳斥了书面语言符号的“第二性”。汉字具有超稳定性,不仅经受住中华文明几千年社会文化的变迁,甚至可能是维系中华文明延续的载体,这对“能指—所指”的任意性对立构成了挑战,汉字的图像性或许是其根源。这对世界其他非表音文字的研究具有深远的语言学意义。
再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回应中国现实问题。除了继续加深语言文字的本体研究,更要进一步发扬新中国成立以来形成的语言文字工作传统,加强在语言学领域中服务国家、服务党中央的研究工作。例如,形成“语言与社会发展”的中国化研究框架,做好语文教育,将语言扶贫、语言康复、乡村振兴中的语言服务、“一老一小”语言服务等实践升华为理论;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学”下的语言学研究,围绕语言在民族交往、文化认同、共同体意识建构中的作用这一核心问题,研究多民族语言接触与演化、汉语方言与少数民族语言的互动,分析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对民族共同体的纽带作用;发展“语言与制度建设”研究,分析语言规范对国家法治建设、党组织凝聚力建设的作用;发展“语言与国家安全”研究,探讨语言资源安全、网络舆情监控、语言人才储备的战略部署;谋划“人类命运共同体”愿景下的语言政策,探讨将汉字树立为中国文化精神标识,展望将汉语推为下一个世界通用语言的可行性路径。
最后,坚持以文明交流互鉴推进学科建设。在树立中国文化和中国语言学主体性的同时,胸怀天下,放眼全球,批判性地借鉴、扬弃、吸收国外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研究。早些年的巴赫金,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元老之一。晚近一些的澳大利亚语言学家韩礼德受其中国导师罗常培和王力的影响,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研究语言的认识论基础,其系统功能语言学注重语言在交际中的表达,彰显了马克思主义语言研究的实践性和整体性。法国学者勒塞尔克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批判了语言学脱离实践、呈现出个人主义的研究取向,试图在语言哲学中树立马克思主义大旗,这也值得关注。
综上,中国马克思主义语言学应立足中国语言事实和现实需求,融合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打造具有中国学术主体性及国际话语实力的语言学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