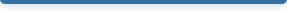◇郎平(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以下简称“世经政所”)在2018年就组建了国家安全研究室,与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室密切合作,共同推进国家安全学科建设。2023年,世经政所国家安全学被确定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重点学科”。基于在该领域的优势和学科积累,世经政所将国家安全学科建设的基本思路确立为:着眼于新时代国家安全重大理论和战略前沿问题,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思想指引,按照理论构建一般形式,探索性地搭建一个新时代国家安全的理论分析框架。近年来,学科团队在重要期刊发表多篇有影响力的学术论文,为新时代国家安全学理论体系建设做出了有益探索。立足当前,下一步学科发展应重点关注两个方面。
确保学科独立性的基石
一般意义上而言,理论体系的构建是一个学科从零散知识积累迈向系统化、成熟化发展的核心标志。它不仅是学科独立性和科学性的基石,更是推动知识创新、指导国家安全实践的框架指引。国家安全学作为交叉学科,具有鲜明的跨学科性。根据国家安全研究所涉领域和维度,与法学、工学、管理学、军事学、区域国别学、经济学等其他学科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融合与交叉。但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国家安全学必须建立起独立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既要普遍适用于国家安全所涉各个领域,还要具有足够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以融汇其他学科领域的知识和分析工具。这既是确保其学科独立性的基础,也是划定国家安全学学科边界的重要支撑。
从这一原则出发,学科团队近年来在国家安全学理论建设中开展了初步探索。张宇燕、冯维江在《新时代国家安全学论纲》等文章中利用经济学、国际关系特别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资源,提出了国家安全学理论体系的五个基本假定、三个基础性概念和五组核心概念,从厘定安全水平、安全能力和安全威胁关系的基本框架出发,得出了七个重要的理论命题。在该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学科团队基于数字经济治理中开放和安全的困境,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视角出发,分析和比较了不同情景下国家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绩效,并围绕经济安全、战略安全、国家安全思想以及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展开研究。如果说概念是理论大厦构建的“砖瓦”,那么理论命题则是对核心概念之间关系的判断,是支撑理论大厦的“骨架”。面对日益复杂的国家安全形势,理论大厦的内容和架构还需要根据实践不断去丰富和完善。
学科发展需要重点突出,特色鲜明。作为属于世经政所整体研究视野下的国家安全学科建设,必须思考的理论问题是,国家安全学科的研究与国际关系的安全研究有什么异同,也即学科边界到底在哪里。安全作为一个基本概念,在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等学科原有的知识体系中,围绕战争、和平、冲突、合作、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等核心概念已经构建起了系统的、多层次的理论框架,基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研究范式和研究路径也发展出了多种不同的理论流派。国家安全学科理论体系作为与国际问题研究密切联系的学科,也已经吸收了这些学科中关于“安全”“国家利益”“国家安全”等被学界主流公认的概念和内涵,但客观而言,尽管内涵有共通点,国家安全学科的基础理论分析框架却应该有所区分。具体而言,两者目标都是实现世界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安全,但国际关系的“国家安全”研究更为关注国家间的安全关系,其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如何通过国家间的互动和博弈来实现国家安全;而国家安全学科的核心内容则是如何理解和认识“安全”本身,例如通过对“安全风险”“安全威胁”“安全挑战”等概念的分析来制定不同的应对策略,其逻辑是如何基于对风险的评估来应对不同的安全威胁和安全挑战。在这两种语境中,“安全”作为研究对象之一都需要被界定、认知,但又因为研究背景和出发点的不同,必须进行明确区分。同理,学科的边界还可以从其他角度去进行多维界定,这也需要学者在未来进一步去深入思考和探索。
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理论通常是对现实高度抽象和系统化的认识,它一方面来源于经验的实践,另一方面好的理论也必须能够指导、反哺实践。国家安全学在设立之初就被确立为交叉学科,正是因其在实践中涉及国家各行各业、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因而,国家安全学的基础理论应该是普适的,是国家各个领域安全实践经验总结的最大公约数,同时它还应该能够解释和指导各领域的国家安全实践;同样,涉及国家安全各领域的具体理论也必须能够体现所涉领域的特点,满足基础理论在具体领域的应用和扩展需要。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国家的总体性,同时明确了20个国家安全重点领域,因而学科基础理论既应该对总体国家安全观具有普遍的解释力,又应能够指导重点领域的安全实践,并且还应在国家安全实践中不断发展创新。
近年来,网络安全、数据安全和人工智能安全的重要性在不断凸显,先后被列入我国的重点安全领域,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也对此提出了明确要求。现实对网络安全、数据安全和人工智能安全提出了共同要求,即在国家治理中必须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二者关系。一方面,这些安全领域都与推动国家经济发展和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基础设施和新动能密切相关;另一方面,它们在实践中又会不断发散、外溢,影响到国家安全的方方面面。
如何理解、认识和应对这些领域的安全风险就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任务和挑战,也逐渐成为学界安全理论研究的前沿发展趋势,相关理论研究对安全工作的指导意义也在提升。例如,“安全是有成本的”反映出安全投入并非越高越好,既要考虑到安全产出的效率,也要兼顾安全水平提高对发展带来的溢出效应;“绝对安全不能实现”和“无意安全和有意安全”则说明,网络空间的安全风险不可能全部消除,当梳理出各个领域存在的安全风险之后,应根据安全威胁的来源和动机分类施策,真正理解和认识这些风险,再根据风险的性质针对性施策应对。
实践为应用和检验理论提供了有力工具,也为进一步在实践中发展国家安全理论提供了支持。同样以网络空间和数字领域的安全风险为例,即使都处于网络和数字智能时代的环境中,不同国家对网络安全、数据安全和人工智能安全的威胁感知差别很大,应对举措也各不相同。这也提示学者在构建理论体系时,应将“安全风险”与“安全威胁”两大核心概念进行精准区分。风险无处不在,但“风险”并非对所有国家都构成安全威胁,是否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还取决于该国的“安全能力”。换句话说,面临同样的外部安全环境,安全能力强的国家能够拥抱风险,而安全能力弱的国家则会感受到更大的威胁。再比如,从网络安全到数据安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场景和内涵也在发生变化。如果说在网络空间治理中,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发展一体两面,作为“驱动之双轮”需要同步推进,那么在数据治理中,安全和发展却不能同时实现最大化。数据越流动,其内在创新潜力就越大,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安全风险也就越大,安全风险和数据流动相伴相生。故而,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理论构建也应适应现实发展,不断创新完善。
加快构建国家安全学理论体系,推动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是新时代赋予国家安全学科的历史使命。目前,世经政所国家安全学科团队着眼于重大国家安全战略和前沿问题,深入推进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学习和阐释工作,逐步探索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以期为维护我国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贡献应有的学界力量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