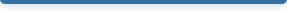黄承梁(生态文明研究所)
《习近平生态文明文选》第一卷(下文简称《文选》)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智慧的深厚土壤,通过历史逻辑的梳理、理论逻辑的阐发以及对现实问题的深切观照,全面、系统、深刻地总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突破、制度创新、实践范式与全球贡献,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生态治理领域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文选》既是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时代升华,也为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提供了系统的方法论和实践论,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理论丰碑与纲领性文献。
彰显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科学完整的理论体系
《文选》收录的79篇重要文献,既有系统全面的理论阐释,包含立足当前的发展方略,又涵盖着眼长远的战略布局,构成了一个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些闪耀着真理光芒的重要论述,为我们正确认识和系统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内涵及规律提供了金钥匙。
第一,构建了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理论框架。《文选》收录的《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等重要文献,系统阐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要义。其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哲学观,深刻揭示了人类文明演进的基本规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发展观,创新性地解决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辩证关系;“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民生福祉”的生态价值观,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生态治理导向;“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观,提供了整体性治理的科学方法论;“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的法治观,构建了制度保障体系;“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全球观,彰显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六大方面相互支撑、有机统一,构成了逻辑严密、层次分明的理论体系。
第二,以“两个结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和中华传统生态文化。《文选》中的理论创新具有三个显著特征。一是理论继承性,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基本原理,继承了“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等经典论断;二是文化主体性,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中国传统生态文化、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理论;三是理论创新性,如《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创造性地将生态环境要素纳入生产力范畴,提出“绿色生产力”概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种理论发展既坚守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回应了新时代实践需求,实现了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统一。
第三,创新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系统思维方式和方法论体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处理好几个重大关系》等文献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深刻揭示并正确处理了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矛盾对立统一关系,深化了对人与自然关系规律和生态文明价值目标的科学认识,指明了建设美丽中国的具体行动路径和根本保障。
系统总结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有机融合的实践范式
《文选》作为指导生态文明建设的纲领性文献,不仅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行动指南,更从根本上为中国式现代化确立了生态逻辑,推动了发展理念、发展方式、治理体系的系统性变革,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实践论。
实践路径的系统建构。一是多维协同治理路径。《文选》提出的“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理念,构建了空间—要素—过程的多维治理框架。这种系统治理路径突破了传统环境治理的碎片化困境,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协同提升。二是绿色转型实践范式。《以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提出的生态产业化路径,创新性地将“两山”理论转化为实践模式。通过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构建了“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转化通道,为新时代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板。
制度创新的体系化突破。一是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建构。《文选》所反映的生态文明制度创新,构建了“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特别是中央环保督察制度的确立,形成了“督政”与“督企”相结合、“问责”与“整改”相衔接的闭环机制,解决了环境治理中的“政府失灵”问题。二是制度协同创新机制。《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提出的制度安排,体现了制度供给的系统性思维。通过构建生态补偿、排污许可、环境信用等制度的协同联动机制,形成了激励相容的制度合力。这种制度设计既避免了“制度孤岛”效应,又防止了“制度拥挤”现象,实现了制度效能的最大化。
现代化发展范式的重塑。一是重构了现代化的发展逻辑。《文选》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在发展目标上,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发展方式上,强调质量效益型增长;在发展评价上,建立包含生态指标的考核体系。二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在产业层面,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体系;在空间层面,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在消费层面,培育绿色生活方式。这种系统性变革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新的实践路径。三是创新现代化治理体系。生态文明建设推动环境治理体系实现了三个转变,即从单一环境治理向全域综合治理转变;从行政主导向多元共治转变;从末端管控向全过程防控转变。这些创新丰富和发展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内涵。
深刻凸显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全球价值和世界意义
《文选》展现的中国智慧,其深层价值在于开创了一种新的文明对话方式。通过将天人合一的东方智慧与现代可持续发展理念相融合,正在推动形成更具包容性的全球生态话语体系,为人类应对生态环境挑战、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路径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具有特殊的参考价值。《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等文献表明,后发国家完全可以在工业化进程中避免重蹈“先污染、后治理”的覆辙。中国探索的“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发展模式,为发展中国家破解经济增长与环境压力的两难困境提供了现实样板。特别是将生态保护与脱贫攻坚相结合的创新实践,展现了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独特作用。
中国的生态文明理念是对西方传统工业文明生态困境的根本性反思与超越。它通过价值理念的重塑和发展范式的创新为世界提供了一个在生态约束下实现可持续繁荣、具有普遍参考意义的系统性框架。《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并非简单地否定经济增长,而是深刻解构了“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二元对立的迷思。它揭示了优质生态环境本身蕴含的巨大经济价值(如生态旅游、绿色产业、健康福祉)和长远发展潜力(资源永续、气候韧性),将生态资本视为发展的核心要素和核心竞争力。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家园。《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努力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等文献超越了传统地缘政治思维的局限,提出共生共存的新型国际关系理念。《文选》强调的“地球生命共同体”“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理念,将人类文明置于更宏大的生态网络中进行审视,既坚持了气候正义的价值立场,又体现了务实合作的行动导向。这种整体性世界观,为破解全球环境治理中的“集体行动困境”提供了思想基础。中国通过南南气候合作、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等实践,推动全球环境治理范式从“规则约束”向“共识引领”的转变,对于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生态秩序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