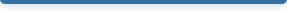◇胡文涛 禹湘(生态文明研究所)
全球经济发展一直面临一个关键性问题,即经济发展必须以环境恶化为代价吗?
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大多走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后发国家能否突破“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路径及其理论制约?近年来,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正在用自身实践给予这一关键问题新的答案,并在这个过程中贡献着独特的理论创新和发展智慧。
理论突破:
发展路径的三重逻辑重构
西方环境经济学的经典理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认为,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呈倒U型关系。在工业化初期,环境恶化不可避免;只有当人均收入达到较高水平后,环境质量才会改善。中国的实践正在改写这一理论预设,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从线性演进到跨越式发展。传统工业化理论遵循“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走向后工业社会”的线性演进模式,每个阶段似乎都不可缺失,无法实现跳跃。而在中国,广袤的地域和多样化的发展进程呈现出一种“时空压缩”特征,在短短几十年中向全世界展现了实现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与绿色化的“五化同步”,并且用“并联式”发展避免重蹈西方“串联式”发展的弯路。
这种跨越式发展为绿色经济发展模式提供了实践路径。在这种模式下,后发国家不必重复过往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演进路径,也可以不受困于在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的传统工业化模式下的奋力追赶,而是直接布局绿色发展的能源、产业赛道,通过技术创新实现跨越式发展。
从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索洛增长模型强调资本和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但忽视了生态约束。中国的新发展理念则是将绿色发展纳入增长函数,强调通过绿色技术创新和生态保护制度创新,提高经济增长中的绿色含量。这并非简单的产业替代,而是发展内涵的根本重塑。传统工业化时代,经济增长主要依赖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的产业。而在绿色发展模式下,经济增长的内容发生转变,节能环保产业、清洁能源、新能源汽车等成为新的增长点,更重要的是可以实现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环境污染的逐步“脱钩”。其中,技术进步的“脱物质化”是这一转变的关键,即当技术水平达到某个临界点后,单位经济产出的物质消耗和环境代价呈指数级下降。绿色技术的快速进步不仅降低了经济发展的环境代价,更创造出新的增长动能,使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持续提升。
从局部治理到系统思维。新古典经济学往往在局部均衡框架下分析环境问题,将其作为“单一性、局部性、外部性”因素进行处理。中国近年来推动的生态文明建设则体现了更为整体、全局、均衡的思想。“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理念正是这种系统思维的体现。生态治理不再是简单的末端治理或单一要素治理,而是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等各类生态要素,一体化实施系统保护和修复。在这种系统论视角下,环保约束不仅不会阻碍经济发展,反而成为倒逼产业转型升级的激励要素,从而实现环境改善与经济增长的双赢。
实践创新:
绿色发展的中国方案
保护生态环境已成为全球共识,但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执政党的执政理念和行动纲领,用思想的高度和理念的深度来引领改革,在世界上尚属首次。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十五五”时期主要目标就包括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绿色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底色,系统阐述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的战略举措。
产业蝶变——从倒逼转型到主动升级。近年来,中国不断加大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和力度,倒逼传统产业在绿色改造中“涅槃重生”,钢铁、水泥等行业通过技术革新华丽升级,走向世界前沿。同时,生态约束构建起新兴绿色产业的长效激励机制。中国不仅建成世界最大的清洁电力系统,更在光伏组件、风电设备、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占据全球市场领先地位,超30万亿元的绿色信贷,为这场深刻的产业革命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金融“活水”,形成“生态倒逼—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效益提升”的良性循环。
区域实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神州大地上结出累累硕果,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塑造出区域崛起的核心竞争力。浙江的“千万工程”开启了乡村振兴的绿色篇章。历经20余年持续推进,浙江乡村从环境整治到生态建设,从“一处美”拓展为“全域美”,从“环境美”升华为“发展美”。生态农业、乡村旅游、文化创意等新业态在青山绿水间蓬勃生长,成为共同富裕的生动实践和美丽中国的基层样板。长江经济带的绿色转型展现流域治理的中国智慧。在“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战略指引下,沿江11省市协同发力,清退沿江化工企业、修复生态岸线、推动产业转型。长江干流水质持续改善,“一江碧水向东流”的场景重现;与此同时,高端制造、绿色航运、清洁能源等新兴产业集群顺势崛起,流域经济实现从“破坏式增长”到“保护式发展”的根本转变,以及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
机制创新——让生态价值可感知可变现。成功实践的背后,是一系列制度性、机制性创新的有力支撑。各地从探索建立“生态银行”搭建资源变资产的桥梁,到推广“碳普惠”机制激励全民践行绿色生活,一系列关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机制创新,正在全国各地破土而出、深化落地。这些制度性探索,系统性地将清新的空气、洁净的水源、美丽的风景这些曾经的“无价之宝”量化、转化、市场化,让守护“好风景”的各方获得实实在在的“回报”,从而让“新产业”拥有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中国的绿色发展实践雄辩地证明,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不是对立选择而是协同共进,绿色转型不是沉重负担而是重大机遇。生态优势正成为区域崛起最坚实、最持久的竞争优势,描绘着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壮丽图景。从理念创新到制度建设,从产业变革到区域实践,中国正在探索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全球意义:
为人类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中国的绿色发展不仅改变着中国,也在影响着世界,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理论创新和实践智慧。
中国的实践丰富了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内涵,证明“后发优势”不仅体现在技术追赶上,更体现在发展路径选择上。通过“弯道超车”和“换道发展”,后发国家完全可以避免“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更重要的是,中国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证明了即使是人口负担大的国家或经济不发达的国家,也可以走绿色发展道路,这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中国不仅是倡导者,更是行动派。在对全球环境治理的机制创新上,这份贡献体现为“行胜于言”的务实行动。在全球治理规则层面,中国积极推动《巴黎协定》的达成与落实。中国在2020年提出“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之后,于今年10月再次提出新一轮国家自主贡献目标。这组涵盖新的减排力度、能源变革、产业转型、气候韧性等多个方面的系统性目标,不仅对照了《巴黎协定》要求,更展现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雄心和担当。
中国始终立足“全人类”,深度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中国成功举办《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推动达成“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尤其是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狭隘的民族国家利益,为南南合作、南北对话提供了新思路。近年来,中国的绿色发展已经从多个方面、多个维度为全球环境治理提供了丰富的有益启示和重要补充,为全球环境治理机制提供了新的思路与借鉴,让绿色成为全球合作的底色,不仅是产品和技术的输出,更是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