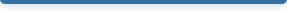◇本报记者 刘远舰
4月24日,“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京揭晓,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发掘的甘肃临洮寺洼遗址入选。近日,本报记者就寺洼遗址新发现的重大意义及相关田野考古工作的新进展,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寺洼遗址考古发掘项目领队郭志委。
彰显黄河上游早期文明发展新高度
《中国社会科学报》:祝贺郭老师,甘肃临洮寺洼遗址入选“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请您先简要介绍一下寺洼遗址的文化内涵。另外,您认为哪些方面值得读者们重点关注?
郭志委:谢谢!寺洼遗址是寺洼文化的命名地,从发现至今已101年了,从我们的老所长夏鼐先生抗战期间的发掘算起,也整整80年了。这处遗址面积超2平方公里,文化内涵极为丰富,涵盖了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寺洼文化及辛店文化遗存,文化序列完整,延续达数千年,是西北地区一处罕见的大遗址。
我们这次公布的主要是马家窑文化的大型聚落。发现了三重长方形布局的围壕(沟)、近百座房址、大量灰坑窖穴、十余座陶窑和数座墓葬,另有疑似“道路”和大面积“人工堆土”的线索,时代从马家窑类型延续到半山类型,在多个方面取得重要突破:首次发现史前时期三重长方形布局的“围壕(沟)”;首次发现马家窑文化大规模制陶区;首次发现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大型聚落;首次确认马家窑文化为高等级、中心性聚落。上述发现展现了5000年前黄土高原西部早期社会的发展水平和文明化程度,彰显了黄河上游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新高度。
《中国社会科学报》:正如您所说,寺洼遗址取得了多方面的重要突破。请您具体介绍一下,这些重要发现具有怎样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对深化中华文明探源研究有何助益?
郭志委:中国考古学100多年以来,史前时期的壕沟发现很多,但多数是大致圆形或不太规则的形状。这次寺洼遗址发现的围壕(沟)不仅有三重,还具有非常规整的平面布局。三重围壕(沟)整体接近东西—南北方向,横平竖直,平行分布,西南角直角转弯,呈长方形布局。现存东西长约600米,南北宽约450米,内部复原面积近30万平方米,应是经过精心规划和测量后修建的大型工程。始建和主要使用年代在马家窑类型时期,距今约5000年。这样的围壕(沟)不仅在马家窑文化中是首次发现,在整个史前时期也是第一次发现,是国内已知最早的多重长方形布局的围壕(沟)结构,其直角转弯特点,为后世长方形“城池”角的出现奠定了早期基础。
提到马家窑文化,大家最熟悉的便是其精美绝伦的彩陶,此前研究也多关注彩陶本身。这次我们在寺洼遗址发掘出了大量与制陶相关的遗迹和遗物,向我们展示了马家窑文化发达制陶业的很多细节和整体面貌,让我们更为清晰地了解到马家窑文化精美的彩陶是如何制作的,并进一步探讨马家窑先民为何对彩陶情有独钟,以及由此展示出来的黄河上游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地域性特点。
至于半山类型聚落,也是一项填补空白的发现。半山类型遗存发现百年来,田野考古发掘出的主要是墓地,极少见到同时期的聚落。因此,很长一段时间内,学界甚至存在半山只有墓地的说法。这次发现的半山类型聚落,是继严文明先生于20世纪60年代在兰州青岗岔遗址发现少量半山房址之后,首次发现较大规模的半山类型房址、灰坑、窖穴和陶窑,与前述半山时期尚未填满的三重围壕(沟)共同组成了半山类型聚落的内容,填补了半山类型聚落发现的空白。此外,半山类型房址内葬人的现象也属首次发现。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实施以来,很多地区尤其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早期文明化进程和模式日益清晰,而黄河上游在相关问题上依然模糊不清,文明探源的很多重要问题尚未触及。马家窑文化正处在黄河上游的核心腹地,年代居于文明探源的关键时期,在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这次寺洼遗址发现的马家窑文化聚落展现了5000年前中华文明西部高地早期社会的发展水平和文明化程度,彰显了黄河上游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新高度,其西北特色丰富了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多元一体”格局,填补了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中西北地区关键时期的空白,成为认识黄河上游早期文明化进程的新起点,实证了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和源远流长。
在百年传承中迎难而上结硕果
《中国社会科学报》:考古发掘工作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长期的坚持与积累。2018年以来,您作为领队一直在参与寺洼遗址的发掘工作,如今终于结下硕果,可喜可贺。请问,在这些年的发掘历程中,您与考古队员们遇到了哪些困难与挑战?有哪些重要时刻给您留下了深刻印象?
郭志委:田野考古发掘和研究确实是一项周期长、见效慢的系统性工作,很多考古发现还具有一定的偶然性,需要极大的耐心和长期的坚守。但这项工作又不可或缺,是一项基础性科研工作,很多科技分析和综合性研究都要建立在这项工作的基础之上。这个项目从立项到现在历时已超过10年,田野发掘从马家窑遗址算起也已有12次了,其间遇到过各种各样的挑战,但最大的挑战还是来自遗址本身,尤其像寺洼遗址这样涵盖多个考古学文化、内涵极为丰富的大遗址,工作难度更是成倍增加。我们最开始的工作更像是盲人摸象,对遗址缺乏整体性认识。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快速找准突破口,先把遗址大的框架性内容认识清楚,建立起遗址整体的时空框架,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
至于印象深刻的时刻,首先能在寺洼遗址这样具有百年发现史,且有珠玉在前、出现在教科书上的著名遗址发掘,一开始当然是兴奋,但后面更多是巨大的压力。加之我们这个团队人员少,所里老师经常是1人。所以,前期阶段线索不清晰时,大家常常很迷茫。但所里对我们很包容,给予我们很大的耐心和多方面支持,使我们有信心最终坚持了下来。越往后做,线索越多,每项新的发现和突破都会让大家兴奋不已。做到现在,一些新收获其实是有意识找出来的,而不是偶然碰到的。每次预设一个想法,再到探方里去验证,验证成真的时候,大家都会成就感“爆棚”,真的感觉像是和几千年前的远古先民连线成功了一样,“好玩”极了。
《中国社会科学报》:甘肃地处西北,自然环境相对恶劣,发掘条件比较艰苦。党的二十大以来,院党组高度重视和关心考古发掘一线工作人员的工作与生活状况,着力改善工作环境、提升有关人员待遇,为顺利开展高质量的考古发掘工作保驾护航。您能谈谈近几年考古工地上都发生了哪些变化吗?
郭志委:确实感受挺深的。我们在发掘期间,常常会翻阅遗址早年的工作资料。101年前,安特生来到这里,让学界知道了这个遗址。整整80年前,同样在4月份,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我们的老所长夏鼐先生来到这里发掘,做了开创性的工作。翻看夏鼐先生留下的日记和当时发掘的照片,寻找夏鼐先生当时租住的房子和布设的探方,再对比现在的工作,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了时代的变迁和祖国如今的强大。同样,这些年从院党组到所党委,都高度重视考古工作,尤其是一线的田野工作,给大家解决了很多实际困难。比如,技师待遇问题,大幅提升了技师的工资和绩效,稳定了技师队伍,保障了田野工作的顺利开展。再如,给一些站队大幅改善了工作条件,让大家可以更好地开展各项工作。总之,大家都切实感受到了院党组和所党委对田野一线人员的关心与厚爱。
坚定信念助力中华文明探源新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报》:考古发掘工作不只有田野发掘,还涉及田野调查、勘探、绘图、文物修复与保护等上下游多方面工作,是一项系统性的复杂工程。作为考古队队长,请您从切身感受出发,谈一谈近年来院里对考古发掘工作的重视与支持。
郭志委:确实,考古发掘看着像是到地里挖土,实际上是一项系统性工作。从团队的组建到人员的吃喝拉撒睡;从工人的招募到组织管理,再到与各级部门的协调;业务工作从遗址的调查勘探到发掘,再到资料的整理与综合研究,是一项周期长、内容庞杂的系统性工作。近些年,院党组和所党委从体制机制上加强了对一线田野工作的管理,实施了一系列重要举措,梳理、规范了很多业务流程,完善了规章制度,保障了相关工作的顺利开展。尤其是对考古队队长,作为田野考古现场的第一责任人,从院里到所里都高度重视,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加强了党性教育学习和相关业务培训,对大家严管厚爱,确保田野发掘工作安全、有序、高效推进,为深化中华文明探源研究提供高质量的考古发掘成果。我相信,在院里和所里一如既往的支持下,未来各队的田野发掘工作将佳绩连连,助力中华文明各项研究取得新突破。
《中国社会科学报》:未来,寺洼遗址的发掘工作将如何继续展开?还有哪些方面值得我们持续关注?
郭志委:前面已经提到过,寺洼遗址发现至今已经101年了,工作虽有中断,但也延续了100年。对于这样一个内涵丰富且具有重要地位的关键性大遗址,我们应该把相关发掘工作继续下去。现在,我们对整个遗址的框架已经有了突破性认识,下一步需要把围壕(沟)内侧的聚落内容搞清楚,厘清其具体布局和功能;进一步在围壕(沟)外围寻找其他重要线索,比如同时期大型建筑或设施、马家窑类型墓地等。同时,齐家文化聚落和寺洼文化聚落的相关工作也应逐步开展起来,力争把这个遗址做成像殷墟、二里头、良渚等遗址一样,成为“典范”,成为认识黄河上游早期文明化进程的关键性大遗址。